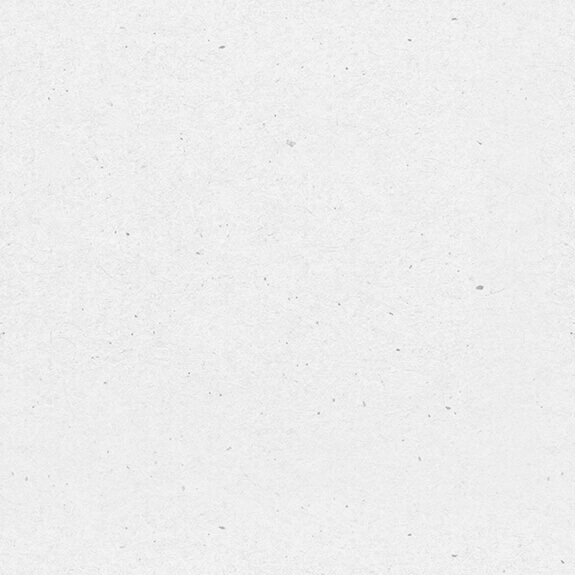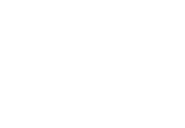05
Feb. 2020
「談文學改編電影」:中山73二月份講座
2/1(六)「談文學改編電影」中山73電影講座
講者:黃以曦
我們今天就將文學改編電影認定為一個現成的詞,來討論什麼是改編?什麼是文學?什麼是電影?這些看起來很日常的詞彙,它可能都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豐富有趣。這幾年越來越難看到原創性的電影。好像說故事這件事,現實中永遠會有更好的故事;要做細膩的情節,文學家永遠比編劇有更好的點子。大家似乎漸漸覺得,我們沒有辦法憑空想像一個完全為了電影的本質而打造的故事,必須依賴這個世界上有趣、戲劇化的事件。因此,當我們太習慣去看到改編電影的時候,就應該來看看有哪些種類的電影改編。
電影改編面面觀
比如歷史改編,最近在上映的山姆曼德斯的《1917》,儘管它也有特定的人物、事件,但它更瞄準的是去重現歷史氛圍,藉由人物去讓你看到後面的時空,去傳達那個時候是什麼樣的緊張氛圍、是如何處在一個強烈的低氣壓等等。改編真實事件的電影,通常會將焦點放在人物之間的性格、角色之間的互動,從中去了解原來現實世界有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還有傳記改編電影,實在太多例子了。會被拿來寫成傳記,通常都已經有了某種波瀾壯闊的人生,那種戲劇化的過程常常是電影所偏好的。這樣的過程其實經歷了一個二度的轉換,一個重複貫穿到尾、十分鮮明的人物。你要去想像他原本在現實生活的樣子時,會需要經歷兩個層次的反推,才能勾勒原本的樣子。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根據一篇文章就能改編成電影。所以當我們在講改編電影,並認為這是一個很理所當然的詞彙時,會發現有些改編是從一本書去濃縮,有些是從一篇文章去增加血肉。那改編究竟是怎樣的概念呢?改編是剪裁嗎?是濃縮嗎?是轉換嗎?還是改編有時是一個創造性的部分?這些都是我們在討論改編時可以去思考的東西。
另外,電視劇改編又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轉化過程,前面講的是經過事實、文字的面向去轉變為影像的過程。而電視跟電影的媒介實在太過相像,除了長度的增加、電影感要怎麼去建立,這也是電視改編電影一個很有趣的面向。
最後講到舞台劇的改編。舞台劇和電影是既相像、本質上卻完全不同的兩種媒介。可是同樣作為虛構、表演的藝術作品,更重文學性的舞台劇,搬進影像佔了更大比例的電影裡,是會對原本的劇本造成加分還是威脅?這也是舞台劇改編電影可以思考的東西。
改編電影雖然已經是常態,但去注意它是從什麼樣的媒介轉換過來,去關心它原本的媒介,便會對兩者都有更深入的想法。去思考一個故事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呈現出來,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也很有趣。
《莒哈絲的漫長等待》
《莒哈絲的漫長等待》可以說是雙重的文學改編電影,為作者一本名為《痛苦》的半自傳小說改編而成。無論是原創電影或是改編劇本,只要主角是文學家,我們便可以想像這個電影有個任務,那就是要呈現文學家看待世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電影導演也需要不斷地去揣摩文學是什麼,並用文學的角度來看待世界。這部片在某種意義上,其實可以拍成諜報片,但是當它放在一個文學的框架裡,重點並不在於如何去取得情報,而是描繪一個人在承受這樣巨大的愛情失落和未知的煎熬,並且同時帶著十分大的格局性去描述這個世代。
《此情可問天》、《墨利斯的情人》

這兩部片都是由E. M. 佛斯特的小說改編而成的,導演詹姆士艾佛利的作品常常被人認為「這就是文學改編電影」。一方面他在電影裡面保留了文學的細膩,一方面他去追索、探測人內心細微的情感波動。且詹姆士艾佛利和他的製片在前幾年有一部很有名的作品,叫做《以你的名字呼喚我》,這也是一部小說改編的電影,原作是一部十分意識流的文學作品,電影改編卻能把小說中這些線索串起一個軸線,再把之中精彩、華麗又繁複的情感,謹慎地各個配置到電影發展的軸線裡。
《墨利斯的情人》則像《莒哈絲的漫長等待》一樣,也是作者的半自傳電影,描述同性戀身分在那個時代的壓抑和痛苦。不只可以看見一個人被困在禁忌的情感裡,還可以看見藝術家對這樣的痛苦有著著迷和自我戲劇化的成份在裡頭。一方面憎恨這樣的痛苦,一方面又沉溺其中展現的無限美感。
《女人的一生》
這部片為莫泊桑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提起莫泊桑,就像是某種文學巨擘、高不可攀的存在。但如果試著去看原著的話,會發現劇情實際上是很典型的肥皂劇,描寫了一個女人一生經歷的各種戲劇化、情感的、家庭劇似的情境,因此在當時的年代是十分暢銷的。當電影作者將這樣的故事搬上大銀幕時,他是懷抱著對經典的崇敬之心,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回應喜愛莫泊桑、懷有古典之心的觀眾,在挑選情節轉換成電影時,他更注重情感的深刻性,而反之將情節起伏淡淡帶過。因此相較於莫泊桑的原著,我認為《女人的一生》電影版反而更有藝術性,這也是改編的魔力之一。
《藝想巴黎》
我覺得這部片出現在影展裡是非常有趣的。事實上這部電影是原創電影,並非從任何小說或書本改編而來。但去看完電影後,你會認為這個安排完全合理、完全沒有異議,你可以想像他們就是完全在攝影棚裡拍完一切,劇情類似《愛在黎明破曉時》,主角們兩人從頭講到尾,漫遊在城市裡,在不同的地方停下來,有相應的對話。但是到了《藝想巴黎》之中,城市都是佈景、都是畫出來的,在電影裡面,每一個元素都由角色自己的口中說出來,所以如果他的語言能夠說服你他是這樣子的人、是這樣子的心情,這個故事發生的方式其實是跟文學很相近的。
其實超級英雄電影也是在綠幕、攝影棚拍攝完成。在這些很乾、很貧瘠的場景裡,你必須去想像、詮釋那些激情、壯闊、憤怒的情緒,但其實你所在的地方什麼也沒有。而《藝想巴黎》也是。我去想像原本的場景且來回比較、思考的過程中,我會認為這是在探索我們為什麼會相信?幻覺是如何發生的?我們每一次的入戲,都是一種受騙,都是走入一種幻想當中。當螢幕上呈現的東西假到不行的時候,我們還是能被說服、被感動,那我們是不是比想像的更脆弱?又或我們在相信一件事情背後的機制可以如此複雜,不再是我們單單認定的現實與虛假。
《愛情陷阱》
從劇本去了解的話,會發現這又是一部雙重改編電影。不同於文學的雙重改編,第一重是舞台劇改編成電影的版本,第二重則是空間上的改編。由於舞台劇一般來說不太會改變背景,通常都是在單一場景而有密度很高的對話在裡面。可是當初在製作這齣戲時,他們去拍攝了劇院的各個角落,讓故事發生的空間就是你身處在的大劇院的各個角落。且意外的是當這個空間被重組、被重建時,居然可以在裡頭上映一齣權貴家庭劇,並且還能毫無違和。
當我們在讓整個空間上演各種劇情時,通常會把焦點放在自己身處的世界,但你有沒有想過空間可能會誘惑你、誤導你或是提示你,讓你誤以為這是你自己決定的選擇。因此《愛情陷阱》不只可以看見一個階級差異之間的愛情故事,也可以從空間中去看見雙重改編發生的過程。
電影本身的文學本質
當我們在討論文學改編電影的時候,有時都會誤會電影只能夠是一些很渲染的、很強大的、很直接的一種印象或激情式的東西。可是事實上,電影有時候它不需要依賴文學的本質。電影本身就可以以它的緩慢、以它的逼近或者是遠離,以它各種影像化的狀態,來成就所謂的文學。同樣的,文學不是要改編成電影才會獲得它的影像、獲得它的意象、獲得它的場面。文學用文字的本身,就是那麼乾的、完全是鉛字的排列組合。可是僅僅是那些字,它就可以浮現出一張風景。所以說,電影本身就可以有它的文學性,而文字也本身就有它的影像性。
返回前頁
講者:黃以曦
我們今天就將文學改編電影認定為一個現成的詞,來討論什麼是改編?什麼是文學?什麼是電影?這些看起來很日常的詞彙,它可能都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豐富有趣。這幾年越來越難看到原創性的電影。好像說故事這件事,現實中永遠會有更好的故事;要做細膩的情節,文學家永遠比編劇有更好的點子。大家似乎漸漸覺得,我們沒有辦法憑空想像一個完全為了電影的本質而打造的故事,必須依賴這個世界上有趣、戲劇化的事件。因此,當我們太習慣去看到改編電影的時候,就應該來看看有哪些種類的電影改編。
電影改編面面觀
比如歷史改編,最近在上映的山姆曼德斯的《1917》,儘管它也有特定的人物、事件,但它更瞄準的是去重現歷史氛圍,藉由人物去讓你看到後面的時空,去傳達那個時候是什麼樣的緊張氛圍、是如何處在一個強烈的低氣壓等等。改編真實事件的電影,通常會將焦點放在人物之間的性格、角色之間的互動,從中去了解原來現實世界有這樣子的事情。
然後還有傳記改編電影,實在太多例子了。會被拿來寫成傳記,通常都已經有了某種波瀾壯闊的人生,那種戲劇化的過程常常是電影所偏好的。這樣的過程其實經歷了一個二度的轉換,一個重複貫穿到尾、十分鮮明的人物。你要去想像他原本在現實生活的樣子時,會需要經歷兩個層次的反推,才能勾勒原本的樣子。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根據一篇文章就能改編成電影。所以當我們在講改編電影,並認為這是一個很理所當然的詞彙時,會發現有些改編是從一本書去濃縮,有些是從一篇文章去增加血肉。那改編究竟是怎樣的概念呢?改編是剪裁嗎?是濃縮嗎?是轉換嗎?還是改編有時是一個創造性的部分?這些都是我們在討論改編時可以去思考的東西。
另外,電視劇改編又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轉化過程,前面講的是經過事實、文字的面向去轉變為影像的過程。而電視跟電影的媒介實在太過相像,除了長度的增加、電影感要怎麼去建立,這也是電視改編電影一個很有趣的面向。
最後講到舞台劇的改編。舞台劇和電影是既相像、本質上卻完全不同的兩種媒介。可是同樣作為虛構、表演的藝術作品,更重文學性的舞台劇,搬進影像佔了更大比例的電影裡,是會對原本的劇本造成加分還是威脅?這也是舞台劇改編電影可以思考的東西。
改編電影雖然已經是常態,但去注意它是從什麼樣的媒介轉換過來,去關心它原本的媒介,便會對兩者都有更深入的想法。去思考一個故事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呈現出來,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也很有趣。
《莒哈絲的漫長等待》

《莒哈絲的漫長等待》可以說是雙重的文學改編電影,為作者一本名為《痛苦》的半自傳小說改編而成。無論是原創電影或是改編劇本,只要主角是文學家,我們便可以想像這個電影有個任務,那就是要呈現文學家看待世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電影導演也需要不斷地去揣摩文學是什麼,並用文學的角度來看待世界。這部片在某種意義上,其實可以拍成諜報片,但是當它放在一個文學的框架裡,重點並不在於如何去取得情報,而是描繪一個人在承受這樣巨大的愛情失落和未知的煎熬,並且同時帶著十分大的格局性去描述這個世代。
《此情可問天》、《墨利斯的情人》


這兩部片都是由E. M. 佛斯特的小說改編而成的,導演詹姆士艾佛利的作品常常被人認為「這就是文學改編電影」。一方面他在電影裡面保留了文學的細膩,一方面他去追索、探測人內心細微的情感波動。且詹姆士艾佛利和他的製片在前幾年有一部很有名的作品,叫做《以你的名字呼喚我》,這也是一部小說改編的電影,原作是一部十分意識流的文學作品,電影改編卻能把小說中這些線索串起一個軸線,再把之中精彩、華麗又繁複的情感,謹慎地各個配置到電影發展的軸線裡。
《墨利斯的情人》則像《莒哈絲的漫長等待》一樣,也是作者的半自傳電影,描述同性戀身分在那個時代的壓抑和痛苦。不只可以看見一個人被困在禁忌的情感裡,還可以看見藝術家對這樣的痛苦有著著迷和自我戲劇化的成份在裡頭。一方面憎恨這樣的痛苦,一方面又沉溺其中展現的無限美感。
《女人的一生》

這部片為莫泊桑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提起莫泊桑,就像是某種文學巨擘、高不可攀的存在。但如果試著去看原著的話,會發現劇情實際上是很典型的肥皂劇,描寫了一個女人一生經歷的各種戲劇化、情感的、家庭劇似的情境,因此在當時的年代是十分暢銷的。當電影作者將這樣的故事搬上大銀幕時,他是懷抱著對經典的崇敬之心,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回應喜愛莫泊桑、懷有古典之心的觀眾,在挑選情節轉換成電影時,他更注重情感的深刻性,而反之將情節起伏淡淡帶過。因此相較於莫泊桑的原著,我認為《女人的一生》電影版反而更有藝術性,這也是改編的魔力之一。
《藝想巴黎》

我覺得這部片出現在影展裡是非常有趣的。事實上這部電影是原創電影,並非從任何小說或書本改編而來。但去看完電影後,你會認為這個安排完全合理、完全沒有異議,你可以想像他們就是完全在攝影棚裡拍完一切,劇情類似《愛在黎明破曉時》,主角們兩人從頭講到尾,漫遊在城市裡,在不同的地方停下來,有相應的對話。但是到了《藝想巴黎》之中,城市都是佈景、都是畫出來的,在電影裡面,每一個元素都由角色自己的口中說出來,所以如果他的語言能夠說服你他是這樣子的人、是這樣子的心情,這個故事發生的方式其實是跟文學很相近的。
其實超級英雄電影也是在綠幕、攝影棚拍攝完成。在這些很乾、很貧瘠的場景裡,你必須去想像、詮釋那些激情、壯闊、憤怒的情緒,但其實你所在的地方什麼也沒有。而《藝想巴黎》也是。我去想像原本的場景且來回比較、思考的過程中,我會認為這是在探索我們為什麼會相信?幻覺是如何發生的?我們每一次的入戲,都是一種受騙,都是走入一種幻想當中。當螢幕上呈現的東西假到不行的時候,我們還是能被說服、被感動,那我們是不是比想像的更脆弱?又或我們在相信一件事情背後的機制可以如此複雜,不再是我們單單認定的現實與虛假。
《愛情陷阱》

從劇本去了解的話,會發現這又是一部雙重改編電影。不同於文學的雙重改編,第一重是舞台劇改編成電影的版本,第二重則是空間上的改編。由於舞台劇一般來說不太會改變背景,通常都是在單一場景而有密度很高的對話在裡面。可是當初在製作這齣戲時,他們去拍攝了劇院的各個角落,讓故事發生的空間就是你身處在的大劇院的各個角落。且意外的是當這個空間被重組、被重建時,居然可以在裡頭上映一齣權貴家庭劇,並且還能毫無違和。
當我們在讓整個空間上演各種劇情時,通常會把焦點放在自己身處的世界,但你有沒有想過空間可能會誘惑你、誤導你或是提示你,讓你誤以為這是你自己決定的選擇。因此《愛情陷阱》不只可以看見一個階級差異之間的愛情故事,也可以從空間中去看見雙重改編發生的過程。
電影本身的文學本質
當我們在討論文學改編電影的時候,有時都會誤會電影只能夠是一些很渲染的、很強大的、很直接的一種印象或激情式的東西。可是事實上,電影有時候它不需要依賴文學的本質。電影本身就可以以它的緩慢、以它的逼近或者是遠離,以它各種影像化的狀態,來成就所謂的文學。同樣的,文學不是要改編成電影才會獲得它的影像、獲得它的意象、獲得它的場面。文學用文字的本身,就是那麼乾的、完全是鉛字的排列組合。可是僅僅是那些字,它就可以浮現出一張風景。所以說,電影本身就可以有它的文學性,而文字也本身就有它的影像性。